以前他在铁路上工作,开那种绿皮火车,哐当哐当的,一跑就是好几天不着家。小时候,我对“爸爸”这个概念很模糊,更多是电话里那个带着杂音的声音,还有妈妈总指着铁路说“你爸从这条线上回来”。
后来他退休了,我以为终于能天天见到他了。可奇怪的是,他在家的时间反而更少了。
他总是背着手在屋里转悠,从阳台到厨房,来回十几趟,然后突然停下来,看着窗外说:“我回家了。”
第一次听见这话,我正看电视,随口应了句:“爸,您这不就在家吗?”
他没回头,还是望着窗外:“我说我回家了。”
后来这句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。吃完饭,他放下碗筷:“我回家了。”下午睡醒午觉,揉揉眼睛:“我回家了。”甚至晚上看完新闻联播,他也会站起来,像是要出门的样子:“我回家了。”
我妈悄悄拉我到一边:“别管他,老了都这样。”
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。那种感觉很奇怪——明明他人就在眼前,却一遍遍说要回家。好像我们这个家,这个有我和妈妈、有他所有东西的地方,反而不是他的家。
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,跟着他出了门。我想看看他到底要去哪儿。
那天下午他又说“回家了”,然后慢悠悠地下楼。我在后面隔着十几米跟着。他走得很慢,背着手,沿着小区那条走了二十多年的路,拐过菜市场,穿过小公园,最后在铁路职工宿舍的老楼前停下了。
那栋楼快要拆了,窗户都没了几扇。他就站在楼下,仰着头看四楼那个阳台,看了很久很久。有邻居路过打招呼:“老李,回来看看啊?”他笑着点头:“回家了。”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——他的“家”,是四十年前他和我妈结婚的那间单身宿舍,是他每次出车回来妈妈亮着灯等他的地方,是我还不会走路时在学步车里撞来撞去的那个小房间。
而现在这个三室两厅、装修一新的房子,对他来说,可能只是个“住的地方”。
明白了这一点,我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凿了一下,空了一块。
今年春天,我带他回了一趟老宿舍。楼道里堆满杂物,墙皮剥落得厉害。我用钥匙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,屋里空荡荡的,只有阳光从没玻璃的窗户照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跳舞。
我爸却突然活泛起来。他指着墙角:“电视原来放这儿,你妈最爱看《渴望》。”又指着厨房门口:“你小时候在这儿摔过一跤,额头缝了三针。”走到阳台,他眼睛亮了:“就在这儿,我教你认火车——那是货车,那是客车,红皮的是快车……”
他在空屋子里走来走去,每一步都踩在回忆上。那一刻,这个破败的空房子因为他而变得满满当当。
“爸,”我轻声问,“这就是您说的家吗?”
他愣了一下,然后慢慢点头,又摇头:“也不全是。”他走到窗边,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铁路线,“家是……是跑完那趟车,知道有个地方亮着灯等你。是你妈在阳台上看见我的火车经过,会挥一挥晾衣杆。是你小时候,每次听见火车汽笛,就跑到阳台喊爸爸。”
他转过身,眼睛有点湿:“现在不开车了,那条线不归我跑了。你妈前年走了,阳台空了。你长大了,有自己的日子要过。我每天醒来,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去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原来他说的“回家”,是回到还有方向、还有等待、还有人需要他的那些年。
现在他每次说“回家了”,我还是会觉得心里空一块。但我不再纠正他,而是会走过去,握住他布满老年斑的手:“爸,我陪您坐会儿。”
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,什么都不说。有时候他会讲起以前开车的趣事,怎么在暴风雪里把车准时开进站,怎么帮一个坐过站的小孩找家人。讲着讲着,他的眼睛就会亮起来,像是又握上了熟悉的操纵杆,奔跑在属于他的轨道上。
我知道,那个他心里永远亮着灯的家,有一部分已经跟着妈妈一起走了,有一部分留在了铁轨尽头,还有一部分,也许就藏在我和他共同的记忆里。
昨天晚上,他又站在阳台自言自语。我走过去,听见他说:“最后一趟车进站了,该回家了。”
这次我说:“爸,我在这儿呢。”
他回头看了我很久,像是终于认出来了,笑了笑:“是啊,你在呢。”
那一刻,心里的那个洞好像被补上了一点点。我明白了,他找不到回家的路,那我就成为他的路。他怀念那些亮着灯的夜晚,那我就为他点亮眼前的灯。
也许对我们每个人来说,“家”从来都不是一个地方,而是那些让你知道自己被等待、被需要、被记住的瞬间。当爸爸一遍遍说要回家时,他是在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位置。
而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——每当他说“回家了”,我就走过去,看着他的眼睛,很认真地说:
“爸,咱们已经到家了。”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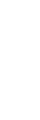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