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话听着可能有点怪,哪对夫妻不红脸呢?我们也红脸。为着鸡毛蒜皮,为着工作上的烦心事,为着对某件事不同的看法,声音也会不自觉地拔高,话赶着话,像绷紧的弦。最后总有一方——多半是他——猛地刹住车,转身就走,留下“砰”的一声不轻不重的关门声。空气里霎时安静下来,只余下我自己的心跳,还有满屋子没吵完的、带着刺儿的委屈。
这,便是我们之间的“冷战”了。
它不像严冬,倒像一场闷热的、酝酿着雨的夏夜午后,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会坐在沙发上,或者躲进书房里,心里翻江倒海,把刚才的争执在脑子里一遍遍重演,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,越有理就越觉得委屈。他呢,通常是把自己关在阳台,对着窗外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发呆,或者干脆下楼,不知去向。
这沉默的时光,短则半小时,长则一两个钟头。它是一道鸿沟,横亘在我们之间,谁也不肯先抬脚迈过去。先开口的那个人,仿佛就输了阵仗,矮了气势。我常常咬着牙,心里暗暗发誓,这次绝不先低头。
可这决心,总会在某个时刻,被一种熟悉的声音,和一种更熟悉的气味,不动声色地瓦解。
那声音,先是钥匙在锁孔里轻轻的转动——他回来了。接着,是厨房里传来的,一系列我闭着眼睛都能分辨的声响:冰箱门被拉开又合上的闷响,自来水“哗”地注入锅中的清冽,然后是“咔哒”一声,燃气灶跳起一簇幽蓝的火苗。
再然后,那气味便来了。
起初是若有若无的,是猪油在热锅里慢慢融化时,那股子醇厚的、带着烟火气的荤香。接着,“刺啦”一声,是切得细细的葱花和蒜末被丢进热油里,瞬间爆出的那股子辛烈又焦香的灵魂。这味道像一只无形的手,一下子就攫住了你的嗅觉。紧接着,是生抽淋入锅沿那股带着焦糖气息的酱香,是老陈醋点进去时那酸冽激灵的一窜,最后,是滚水冲入,那所有味道瞬间融合、升华成一股浓郁、温暖、带着家的妥帖气息的汤底。
而这一切繁复的前奏,都是为了迎接那一把雪白筋道的面条。它们被妥帖地放入翻滚的水中,用筷子轻轻划散,在咕嘟咕嘟的泡泡里,变得柔软而丰盈。
我知道,那是我的面。
是我打小就爱吃的那碗阳春面,或者说,是他为我改良了无数次的,独属于我的“阳春面”。面是他特意去城南那家老面铺买的,比寻常的挂面要劲道许多;汤底他不用味精,总要用一小块猪油,说是这样才香得厚实;葱花要碧绿,醋要酸得透亮,最后,必定还要卧一个溏心蛋,蛋黄像一枚小小的、流动的太阳。
当这一切声音与气味交织成的序曲完毕,他会走到书房门口,或者客厅沙发旁,并不看我,只是声音闷闷地,带着点残余的别扭,说:
“面好了,再不吃就坨了。”
就这么一句。没有道歉,没有“我们和好吧”,更没有对刚才争执的评判。仿佛那一个多小时沉闷的、令人窒息的冷战从未发生过,他只是像往常任何一个平凡的傍晚一样,为我煮了一碗宵夜。
而我呢?我会磨蹭一会儿,仿佛是在捍卫自己最后那一点点可怜的“立场”。但脚步总是不听使唤地,被那香气牵着,挪到厨房。那碗面就放在我常坐位置的前面,热气袅袅地升腾着,模糊了灯光,也模糊了我的眼眶。
我坐下,拿起筷子,先小心地戳破那个溏心蛋,看着金黄的蛋液缓缓流出,混入酱油色的汤里,给那汤又添了一层暖融融的厚度。然后挑起一筷子面条,吹一吹,送入口中。面条滑溜筋道,汤汁咸香适中,带着猪油的润、葱花的辛、醋的微酸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一口热汤面下肚,仿佛不只是暖了胃,也把心里那些纠结的、尖锐的、冰冷的东西,都给温柔地熨帖开了。吃着吃着,那些委屈和怒气,就像碗上的热气一样,不知不觉地散掉了。
这时候,他通常会坐在我对面,手里拿着一份报纸,或者就那么看着窗外,依旧不说话。但整个屋子的气氛,已经完全不同了。那层无形的、冰冷的隔膜,被这碗面的热气,彻底融化了。
我会把汤都喝得干干净净,然后放下碗,发出满足的一声轻叹。他便会起身,默默地收拾碗筷,拿到水池边去洗。水流声哗哗地响着,伴随着碗碟轻微的碰撞声,那是我们这个家最平常、也最安心的背景音。
有一次,我忍不住在吃完面后,带着点鼻音问他:“你怎么每次都这样?”
他背对着我,在水池边忙活,头也没回,只是声音平平地说:“不然呢?跟你接着吵?你那个脾气,吵又吵不赢,气坏了身子,还不是我心疼。”
还有一次,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你这算不算是‘食物收买’?”
他这回转过头,看了我一眼,嘴角似乎有隐隐的笑意,说:“收买你干嘛?你这个人,又没啥大用。就是想着,你一生气就不吃饭,胃不好,饿着肚子更睡不着。”
我怔住了,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
原来,他煮这碗面,从来不是为了争论对错,也不是什么求和的策略。他只是在用他最熟悉、最笨拙的方式,照顾我的身体,安顿我的情绪。在他那里,道理可以暂时搁置,矛盾可以容后再议,但我的胃和我的睡眠,是当下第一等要紧的事。
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,有一次我生病,没胃口,他问我想吃什么,我随口说,想吃小时候妈妈做的那种简单的阳春面。他当时没说什么,后来却偷偷打电话问我妈妈做法,自己一遍遍地试。我第一次吃到他做的那碗面时,惊为天人,说比我妈做的还好吃。他当时笑得像个孩子,眼睛亮亮的。
从那以后,这碗面,就成了我的“专供”。我工作累了,他会煮一碗;我心情低落,他会煮一碗;我们吵架了,他更会煮一碗。
这世上的爱,有千百种表达。有的热烈如玫瑰,有的深情如诗歌。而我的他,给我的爱,就是这一碗朴素的、热腾腾的面。它不讲道理,不论对错,它只是在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冰冷僵硬的时候,用最直接的温度和滋味告诉你:无论如何,都要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。我在这儿呢。
如今,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。争执依旧偶尔会有,那“砰”的关门声也依旧会响起。但我的心,却不再像年轻时那样,会随着那一声响而猛地揪紧,陷入无边的惶恐和猜疑。因为我知道,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。就像乐谱里的休止符,是为了让后面流淌出的,那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协奏曲,和这一碗面的温暖滋味,更加动人。
那碗面,是他无声的语言,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,更是将这琐碎婚姻里一切尖锐磨圆的,最温柔的砂纸。
窗外也许有风风雨雨,屋里我们或许也曾磕磕绊绊,但只要能吃到那一碗他专门为我煮的面,我就知道,这个家,终究是暖的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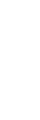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