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是文盲,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。他常说:“娃啊,爷爷这辈子的路就到这儿了,你的路还长。”说这话时,他粗糙的手摸着我的头,眼睛望着山外。
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年级。他最大的愿望,就是我能把书念完。为了我的学费,他什么活都干——上山挖药材,下河捞沙子,去建筑工地扛水泥。有一次他累得晕倒在工地上,醒来第一句话是:“别告诉你妈。”
那年我考上县一中,学费要八百块。晚上我起夜,听见父母在灶房低声说话。母亲在哭:“把猪卖了吧,还差三百。”父亲沉默很久,说:“那是留着过年杀的。”第二天,父亲天不亮就出门了,晚上回来,把皱巴巴的八百块钱放在桌上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去了血站。
高中三年,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。冬天寝室冷,我就到走廊借着灯光看书,脚冻麻了就在原地跺跺。暑假回家,看见父亲的白发又多了,背也更驼了。他把省下的烟钱给我买参考书,自己抽旱烟叶子。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,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。父亲把通知书摸了又摸,不认字的他指着校徽说:“这个图案真好看。”临走前夜,母亲在我行李里塞了十个煮鸡蛋,还有她连夜纳的鞋垫。
大学四年,我同时打三份工——家教、餐厅服务员、图书馆管理员。别的同学在谈恋爱、打游戏时,我在背单词、做习题。每年春节回家,我都用打工的钱给家里买点东西——给爷爷买棉鞋,给父亲买羊毛衫,给母亲买围巾。他们嘴上说浪费,却总是舍不得穿、舍不得戴。
大四那年,深圳一家公司来校招,我过关斩将拿到了offer。签约那天,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月薪六千,他在那头久久没有说话,最后哽咽着说:“好,好,我儿子有出息了。”
工作第一年,我省吃俭用存下三万块。过年回家,我把存折放在父母面前。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敢接,看着上面的数字,眼泪直往下掉:“他爸,咱们有钱还债了。”
这些年在深圳,我从基层做到管理层,成了家,买了房。把父母接来住的第一晚,父亲在阳台上站了很久,看着城市的灯火说:“这一片亮堂,比咱们老家的月亮还亮。”
最让我欣慰的是,我供妹妹读完了大学。她现在是省城医院的医生,去年结婚时对我说:“哥,要不是你,我可能早就嫁人生娃,一辈子困在山里了。”
去年春节,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。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,很多人家盖起了新房。村支书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们这些走出去的孩子,给村里的娃娃们立了榜样。现在大家都相信,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。”
站在老屋前,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大山,我想起爷爷的话。三代人,从爷爷的文盲,到父亲的小学,到我的大学,再到妹妹的研究生;从深山到县城,到省城,再到深圳。这条路,我们走了整整三代。
夜深了,儿子在台灯下写作业。他生在深圳,长在深圳,已经听不懂老家的方言。但我会经常给他讲山里的故事,讲煤油灯的味道,讲他爷爷如何用肩膀扛起一个家的希望。
“爸爸,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?”儿子曾这样问我。
我摸着他的头说:“为了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,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”
改变三代人的命运,听起来像个神话。但我知道,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,用最朴素的坚持,一代人踩着上一代人的肩膀,慢慢从谷底爬上来的真实故事。
山还在那里,但我们已经走出了大山。而更大的山,还在前方等着我们去攀登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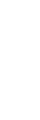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