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是差不多同时搬进来的,成了门对门的邻居。他是厂里的钳工,手特别巧,我家什么东西坏了,喊一声“老陈”,他准提着工具箱乐呵呵地过来。我们俩最固定的“节目”,就是晚饭后一起下楼散步,再一起爬上来。我家在五楼,不高不低,但对年岁渐长的我们来说,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锻炼。
“老李,今天怎么样?腿脚还行?”老陈总是这么问。他比我大几岁,膝盖有点毛病,上楼梯得扶着栏杆,慢悠悠地,一步一顿。
“还行,比你强点儿。”我通常会拍拍他的背,走在他旁边,配合着他的节奏。
我们爬得很慢,一边爬,一边聊。聊儿女的工作,聊菜市场的物价,聊最近看的电视剧,也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。从一楼到五楼,一共七十八级台阶,每一级都听过我们的絮叨。春天,楼道窗户里会飘进樟树的花香,有点冲鼻;夏天,汗衫会湿透,黏在背上;秋天,夕阳的余晖会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投在斑驳的墙上;冬天,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衣,呼出的白气在昏暗的灯光下缭绕。这楼梯,像一条时间的河床,我们的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流淌过去。
老陈的膝盖,一年不如一年。我眼看着他上楼梯越来越吃力,从最初只是慢,到后来需要中途在一楼半、三楼那两个拐角的平台停下来,扶着腰歇口气。我劝他:“老陈,要不咱去看看,换个膝盖?”
他总是摆摆手,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,喘着气说:“老家伙了,换什么换,将就着用吧。再说,这楼梯爬惯了,一天不爬,浑身不得劲。”
我知道,他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,也舍不得那点手术费。于是,我也不再劝。他歇的时候,我就陪他站着,看看窗外那棵一年年长高的香樟树。我们的对话,开始夹杂着更多的喘息声和沉默。
转折发生在前年。社区搞老旧小区改造,征求大家意见,其中一项就是装电梯。消息传来,我们这栋楼可炸了锅。一二楼的住户大多不同意,说用不上,还挡光、有噪音。我们三四五楼的,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,自然是举双手赞成。那段时间,楼道里碰见了,聊的都是电梯的事,邻里之间甚至有了点剑拔弩张的味道。
我和老陈自然是坚定的“装电梯派”。好几次,我看见老陈拉着社区的工作人员,指着自己的膝盖,情绪有些激动地说:“同志,你看看我这腿,你看看!这楼梯,我是真爬不动了啊!”他那双摆弄了一辈子精密零件的手,微微颤抖着。
我挨家挨户去做工作,特别是那几家犹豫的。我说:“咱们都老邻居了,几十年感情。今天是我和老陈爬不动,明天可能就是你们家老人不方便。行个方便,也是给自己留条路。”话说得诚恳,心里却有些发酸。人老了,连上个楼,都要求人。
筹备、设计、签字……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和曲折。那大半年里,我和老陈依旧爬着那七十八级台阶。只是,我们的谈话内容,多了许多对未来的憧憬。
“老李,等电梯装好了,我第一个坐上去!”老陈眼睛发亮,“然后我天天坐它上下楼,去买菜,去公园,气死那些当初不同意的人。”他说着孩子气的话,我们都笑了。
“到时候,我陪你一起坐。”我说。
盼星星盼月亮,施工队终于进场了。那段时间,楼外搭满了脚手架,叮叮当当的噪音不绝于耳,但我们心里是欢喜的。我和老陈常常站在楼下,仰头看着那电梯井道一节一节地加高,像看着一个正在长大的希望。老陈的眼神里,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虔诚的期待。
去年春天,电梯终于正式运行了。很普通的银色轿厢,平稳,安静,按一下按钮,几秒钟就能到家。第一次乘坐时,我和老陈像两个第一次进游乐场的孩子,在里面摸摸这,看看那。门关上的瞬间,轻微的失重感传来,然后就是匀速的上升,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噪音。我们互相看了一眼,都没说话,但嘴角都带着笑。那种轻松,是几十年来,爬楼梯时从未有过的。
自从有了电梯,我们的生活半径仿佛一下子变大了。老陈去公园下棋的次数多了,我也敢去更远的市场买新鲜食材了。上下楼变成了一件毫不费力的事,我们甚至会在没什么事的时候,特意坐电梯下去,再坐上来,只为享受那份便捷。
然而,有些习惯,却悄悄地改变了。
我们不再一起“爬”楼梯了。自然,也就少了那些在楼梯间里慢悠悠的交谈,少了在拐角平台一起喘口气、看看风景的时刻。现在我们在电梯里相遇,通常是点点头,问一句“出去啊?”或者“回来了?”,然后盯着那跳动的数字,“叮”一声,到了,各自回家。对话变得简短、高效,却也失去了那份在缓慢攀爬中滋长出的亲昵和温度。
有一天下午,我独自一人,忽然很想走一走楼梯。我推开那道熟悉的、沉重的防火门,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楼道里很安静,只有我的脚步声空洞地回响。我走得很慢,像当年陪着老陈那样。我看到了墙壁上儿子小时候用粉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,看到了二楼那扇永远关不严的窗户,看到了三楼平台那盆不知谁家放的、已经枯萎的绿萝。阳光透过高处的气窗,照进来,光柱里尘埃飞舞。这一切,都因为缺少了另一个人的陪伴和絮语,而显得格外寂寥。
我忽然明白,电梯装好了,我们轻松了,可那条我们一起走了十几年、承载了我们无数欢笑与喘息、见证了彼此衰老过程的楼梯,也同时被我们遗弃了。它从一条充满生命痕迹的通道,变成了一条备用的、被遗忘的角落。
走到四楼半,我习惯性地停了一下,以为会听到老陈熟悉的喘息声。回头,只有空荡荡的台阶。
我最终没有走完剩下的台阶,而是推开那层的防火门,去坐了电梯。在平稳上升的轿厢里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们得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便利,却也永远地失去了某种笨拙却珍贵的东西。那东西,就藏在那一级级被磨得光滑的台阶里,藏在那些缓慢、疲惫却充满陪伴的时光里。
电梯很好,它让我们的身体得以喘息。但我还是会时常想起,那个需要彼此搀扶着、一步一步丈量生活的年代,想起那个爬楼梯的,我的老伙计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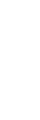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