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听着,也跟着笑,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细细地、密密地扎着,一种熟悉的、绵长的疼,又悄悄地漫了上来。
他的家庭,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样子。妻子温婉,女儿可爱,家里总是充满了笑声。他手机里存满了家人的照片和视频,兴致来了就会翻给我看。视频里,他们一家三口在草地上追逐,他妻子拿着野餐篮,温柔地看着父女俩闹成一团;照片上,他女儿过生日,小脸上糊满了奶油,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。他是真的幸福,那种从心底里溢出来的,踏实而温暖的幸福。
可越是看到他这样的幸福,我心里的疼就越发清晰。这疼,不是嫉妒,更不是怨恨。我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。它像一团潮湿的雾,平时隐在心底,一旦看到他幸福的模样,那雾气便升腾起来,濡湿了所有的感官。
后来我才慢慢明白,我疼的,是那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曾经。我的童年,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。记忆里没有温暖的灯光,只有摔碎的碗碟刺耳的声响;没有其乐融融的晚餐,只有饭桌上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我像一只受惊的小鸟,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,用被子蒙住头,试图隔绝外面那个破碎的世界。我也曾有过那样趴在父亲腿上的机会,可记忆里,父亲的膝盖总是硬邦邦的,他的眉头总是紧锁着,仿佛有化不开的愁云。家的概念,对我来说,是摇摇欲坠的墙壁,是随时可能崩塌的积木。
所以,当我看到他那么自然地把女儿扛在肩头,当他那么顺理成章地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时,我就像一个站在玻璃窗外的人,眼巴巴地看着屋内的炉火,温暖、明亮,却隔着一层冰冷的、无法逾越的屏障。他的幸福,像一面擦得锃亮的镜子,清清楚楚地照出了我心底那片巨大的、无法填补的空白。我为他高兴,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,可那份高兴里,总掺杂着为自己感到的,一丝冰凉的悲悯。
这心疼,还来自于一种清醒的“预见”。我太知道,他此刻所拥有的一切,是多么精致而易碎的琉璃。它需要运气,需要经营,需要双方无数次的退让和包容。我看着他那毫无阴霾的笑容,心里会莫名地升起一股担忧。我怕生活的风浪有一天会打湿他的船舷,我怕琐碎的日常会磨钝最初的柔情。我甚至有一种荒谬的冲动,想告诉他,要握紧,再握紧一点。可我什么也不能说,只能看着他沉浸在幸福里,然后自己默默消化这份毫无来由的、先知般的焦虑。这感觉,就像一个从战场上幸存的老兵,看着一个新兵满怀憧憬地走向他认为的和平之地,明知那里也可能有暗雷,却无法出声提醒,只能眼睁睁看着,心里揪成一团。
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饭。在他家里,那种无处不在的生活气息几乎让我有些无所适从。他妻子会自然地给他整理一下衣领,他女儿会跑过来撒娇要抱抱。这些寻常的互动,在我眼里都珍贵得像博物馆里的展品。有一次,他女儿摔了一跤,膝盖擦破了皮,哇哇大哭。他和他妻子立刻围过去,一个轻声安慰,一个熟练地处理伤口。那一刻,我看着那个被爱和安全感紧紧包裹着的小女孩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想起的,是自己小时候发烧,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,多么希望有一双温暖的手能摸摸我的额头。那种迟来了几十年的委屈,在别人的幸福面前,变得无以复加。
我清楚地知道,我这没完没了的心疼,其实和他无关,和他的幸福家庭也无关。这一切,都是我自己的课题,是我与自己那段不够圆满的过去尚未达成的和解。他的圆满,只是无意中照见了我内心的缺口。我需要面对的,是那个一直躲在童年房间里,瑟瑟发抖的自己。我要走过去,抱抱那个小小的我,告诉他,一切都过去了,你现在很安全。
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。我可能还需要在很多个夜晚,独自咀嚼这份复杂的滋味。为他高兴,也为自己疗伤。
昨天,我们又见面了。他给我看他女儿新画的画,一片歪歪扭扭的绿色,说是“爸爸的草原”。他笑得眼睛都弯了,指着那团绿色说:“你看,我姑娘说我是她的超级英雄,能守护她的一片草原呢。”
我也笑了,这一次,心里的疼似乎轻了一些。那不再是尖锐的刺痛,而变成了一种沉静的、潮湿的感伤,像南方的梅雨天,你知道它一时半会儿不会放晴,但你也知道,它终有结束的一天。
我看着他洋溢着幸福的脸,在心里轻轻地说:真好,你一定要永远这样幸福下去。
而我的心疼,就让它慢慢流淌吧。也许有一天,当我能把自己的那片内心荒原,也浇灌出哪怕一小片绿地时,这疼痛,就会自然而然地,风干在真正的阳光里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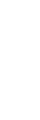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