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声音,我太熟悉了。熟悉到能分辨出每一次“嘟”声之间,那几乎不存在的、细微的停顿。它让我想起很多年前,老家那部老式拨号电话的忙音。那时候,这声音代表着一种确切的“不在”。要么是占线,那头正热络地聊着家长里短;要么是没人接,屋子里空荡荡的,只有电话铃在徒劳地响着。无论是哪种,你心里总还有个着落,知道那头是一个具体的情景,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。
可这一次不一样。我打的是父亲的手机。一个本该随时随地,都能找到他人的号码。从昨天下午到现在,它传来的,就一直是这个声音。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开会,或是信号不好。可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一天过去了,它还是这样。那忙音不再是“不在”的提示,它变成了一种空洞的、没有尽头的回响。它不像占线,占线是有温度的,说明另一个生命正在使用这条线路;它也不像无人接听,无人接听至少还留着一丝希望,期待着下一声铃响就会被拾起。这忙音,是纯粹的、被抽空了内容的拒绝。它仿佛在说,你所拨打的这个号码,连同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个人,已经从这个世界里被轻轻地、却又彻底地抹去了。没有原因,没有解释,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、冷漠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。
我的手指,无意识地在冰凉的桌面上画着圈。脑子里乱糟糟的,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。我想起上一次和父亲通电话,是什么时候?好像就在上周二。他说了什么?我努力地回想。对了,他说,院子里的那棵老石榴树,今年结的果子特别多,沉甸甸的,把枝头都压弯了。他笑着说,等我下次回去,正好能赶上吃,肯定甜。他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,带着一点点沙哑,还有那种老年人特有的、慢悠悠的温暖。我当时在忙什么呢?好像是一边盯着电脑屏幕,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,只“嗯嗯啊啊”地应着,末了说了句“知道了,您自己也注意身体,我这儿还有点事,先挂了。”
“先挂了。”——这三个字,此刻像三根细小的针,扎在我的心上。我挂得那么轻易,那么匆忙,甚至没有让他把关于石榴树的描绘说完。我仿佛能看见,在老家的院子里,他拿着那个旧手机,听着我这头传来的、同样急促的忙音,脸上那一点点笑意慢慢淡下去的样子。他或许会在那棵石榴树下站一会儿,看着满树的果实,然后默默地走回屋里去。
那部老式电话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装的。那时候,装一部电话可是件大事。我记得工人来拉线、装机的那天,父亲像个孩子似的,围着转来转去,一会儿递烟,一会儿倒茶。电话装好了,是那种奶油色的,方方正正的样子,数字键按下去会发出清脆的“哒”声。他拿着话筒,翻着通讯录,第一个打给了远在省城的姑姑,声音洪亮地说:“喂!小妹啊!我家也装上电话啦!号码是XXXXXXX,你记一下!”那份喜悦和自豪,几乎要从听筒里满溢出来。
从那以后,这部电话就成了我和父亲之间最主要的纽带。在外求学的日子,每个周末的晚上,我准会接到他的电话。问的无非是“吃饭了没有?”“钱够不够花?”“学习累不累?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。年少的我,总觉得他啰嗦,常常敷衍几句就想挂断。有一次,我甚至不耐烦地对他说:“爸,这些你上次都问过了,我都好,别总打了。”电话那头,他沉默了一下,然后只是轻轻地说:“好,你好就行。”后来母亲告诉我,那个周末,父亲守着电话机,坐立不安了很久,最终还是没敢再打过来。
工作以后,我更忙了,打电话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。总是他打过来,而我,总是在“开会”、“见客户”、“在应酬”。他渐渐也摸清了我的规律,不再轻易在白天打扰我。那部老电话,像一个忠实的守望者,静静地待在老家客厅的茶几上,它响起的次数,随着年月,无可挽回地稀疏了下去。
后来,我给父亲换了智能手机,教他用微信视频。他学得很慢,手指总是不听使唤,戳不准那个小小的绿色图标。他更喜欢直接打电话,说那样直接,痛快。可我呢,我却越来越习惯于用文字来沟通,觉得高效,省时。他发来的长长语音,我常常是转成文字,扫一眼就完事。我们仿佛生活在两个节奏的时空里,他那头是慢悠悠的田园牧歌,我这头是疾驰的高铁。那根连接我们的电话线,虽然在技术上从铜线变成了光纤,但在情感上,却似乎在变得越来越细,越来越脆弱。
而现在,连这根细弱的线,也彻底断了。只剩下这忙音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它还在响着,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,在寂静中规律地搏动。我忽然想到,这些年来,我是不是一直在挂断父亲的电话?用我的不耐烦,用我的忙碌,用我的自以为是。我挂断了他想分享的石榴树的喜悦,挂断了他小心翼翼的关心,挂断了他那些看似啰嗦实则温暖的唠叨。我把他一点一点地,推向了电话那头无人接听的忙音里。
我是不是,也成了他世界里,一种冰冷的、没有回应的忙音?
想到这里,我的心猛地一缩,一种巨大的酸楚和悔恨攫住了我。我不能再这么听下去了。我猛地按下了挂断键,那折磨人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屋子里瞬间陷入一种更深的寂静。
我站起身,走到窗边。夜色已经浓了,楼下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。我拿起自己的手机,没有半点犹豫,打开购票软件,买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火车票。屏幕上显示,明天清晨六点出发。
然后,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一次,我不再需要那根电话线了。我要亲自回去,回到那个有老石榴树的院子里,走到他面前,看着他也许有些埋怨、但更多是惊喜的眼睛,亲口尝一尝那棵树上结的,今年最甜的石榴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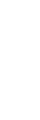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