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现在就躺在我书桌的抽屉里,在一个深蓝色的绒布盒子里。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,笔身是暗红色的,像陈年的枣木,上面有些细小的划痕,金黄色的笔尖已经有些磨损,但擦干净了,依旧能看出一点昔日的光泽。我很少用它,怕磕了碰了,怕墨水干了堵塞它。但每次当我感到特别高兴,或者特别难过,心里有话堵着,非写出来不可的时候,我就会把它请出来,小心翼翼地吸满一管蓝黑色的墨水,然后,翻开我那本厚厚的日记本。
笔握在手里的感觉,是沉甸甸的,凉的。但用不了多久,它就会被我的掌心焐热。这种感觉很奇怪,就好像,我握着的不仅仅是笔,而是爷爷那双布满老茧、温暖又粗糙的手。
爷爷是个小学教师,教了一辈子语文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左上口袋里,就别着这支钢笔。那是我眼里最神圣、最了不起的象征。他批改作业时,身子微微佝偻着,鼻梁上架着老花镜,手里的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,那声音,又轻又稳,像春蚕在啃食桑叶,又像细雨落在瓦檐上。我常常趴在桌边看,觉得那笔尖流淌出来的,不是红色的墨迹,而是知识和道理。
那时候我调皮,总想拿来玩玩,爷爷从不允许。他只是笑着说:“小家伙,这笔啊,有斤两,你现在还拿不动。” 我以为他说的是钢笔本身的重量,很不服气,觉得自己力气大得很。后来才明白,他说的“斤两”,是岁月,是责任,是那些需要一笔一划去承担的人生。
我上中学那年,要住校了。临行前夜,爷爷把我叫到他的书房。昏黄的灯光下,他从上衣口袋里,缓缓地取出了这支钢笔。他用一块柔软的绒布,极其仔细地擦拭着笔身和笔尖,每一个动作都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然后,他双手捧着,递到我面前。
“拿着吧,”他说,“以后,用它好好写字,也好好写写你自己。”
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手上的触感。那沉甸甸的凉意,顺着我的指尖,一下子钻到了心里。我忽然就懂了,我接过来的,不是一件文具,而是一个老人毕生的寄托。他把他认为最郑重、最珍贵的东西,传给了我。
从那时起,这支钢笔,就成了我日记本里唯一的笔。
刚离开家的日子,日记里写的全是想家。我用这支笔,歪歪扭扭地写下食堂难吃的饭菜,写下宿舍里同学的鼾声,写下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的眼泪。笔尖在纸上划过,沙沙声依旧,却仿佛带着爷爷的安慰。好像他在对我说:“别怕,路总要自己走的。”
后来,日记里的内容渐渐变了。有了青春的迷茫和烦恼,有了对某个女孩懵懂的好感,有了考试失败的沮丧,也有了对未来的种种幻想。这支笔,像一个最忠实的、沉默的朋友,承载了我所有秘而不宣的心事。它见过我的泪水——有一次我哭得太厉害,一滴泪落在日记本上,蓝色的字迹瞬间晕开,像一朵忧伤的花。它也见证过我的狂喜——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我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气,在日记本上写下那个好消息,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。
它就这么陪着我,从少年,到青年。
工作后,生活变得忙碌而粗糙。敲键盘的时候越来越多,拿起笔的时候越来越少。有时候,日记会一连空白好几个月。可每当人生遇到重要的节点——升职、恋爱、失恋、亲人离世——我总会下意识地回到书桌前,打开那个蓝盒子,把这支笔请出来。
前年,我最敬重的一位长辈去世,我心情低落到谷底。那天晚上,我一句话也不想说,只是默默地给钢笔吸满墨水,打开了日记本。我写不出任何成形的句子,只是胡乱地画着,任由笔尖在纸上漫无目的地游走。写着写着,我仿佛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沙沙声,感受到了笔杆上那被焐热的温度。我忽然想起爷爷去世时的情景,想起他安详的面容。那一刻,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。这支笔,它送走了我的爷爷,如今,又在陪我送走另一位亲人。它好像一个摆渡人,沉默地载着我,渡过生命里一条又一条悲伤的河流。
它不仅仅是书写工具。它是传承,是陪伴,是我与过去、与亲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、却坚韧无比的丝线。
现在,我偶尔也会用它来给女儿写几句话。她还小,看不懂,只是好奇地摸着冰凉的笔杆,咿咿呀呀。我会告诉她,这是太爷爷的笔。我不知道她将来会不会懂,但我希望,这份沉甸甸的、带着体温的记忆,能够通过这支笔,继续传递下去。
夜深人静时,拧开笔帽,笔尖触及纸张的一刹那,时光仿佛倒流。我还是那个趴在桌边看爷爷改作业的孩子,他还是那个神情专注的老人。沙沙的书写声里,两代人的生命,在这暗红色的笔杆中,悄然汇合。
这支笔,写下的,是我的日记;承载的,是我的人生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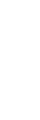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