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送到时我正吃早饭。两个长方形的纸箱,比想象中沉得多。打开一看,全是木板、螺丝、螺母、垫片,还有几包我叫不上名字的小零件。说明书薄薄的几页纸,图示密密麻麻。说实话,第一反应是头皮发麻——我从来不是手巧的人,上次装个简易书架还多出七八个螺丝。
但答应过妻子的。她总说家里缺个能晒太阳看书的地方,网购这款摇椅时,她眼睛亮亮地说:“等你装好了,我就能在那儿喝咖啡了。”
工具摊了一地。我先按说明书把零件分类,长的短的、带孔的不带孔的,在阳台地板上摆成好几排。有个弧形的大件,后来才知道是摇椅的底座。拿起又放下,反复对照图纸上的编号——C板、D板、F条,像在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。
最难的是连接扶手和座板那一步。需要同时对准三个孔,可手只有两只。试到第三次,螺丝刀一滑,左手拇指被划了道口子,血珠冒出来。我进屋找创可贴,妻子要帮忙,我摇摇头:“说好我来装的。”
其实不是逞强。就是觉得,有些事得自己完成。
印象最深的是装弹簧那个环节。十二根小指粗的弹簧,要一头钩住座板下的铁环,另一头钩住底座。第一根我使足了劲,钩上去的瞬间,“砰”一声弹回来,打在木板上嗡嗡响。后来学乖了,用螺丝刀别住一端,慢慢拉伸,听到“咔嗒”一声才算到位。装到第六根时已经满头大汗,T恤后背湿了一片。
但奇怪的是,越装越顺手。拧螺丝找到了节奏——先逆时针转半圈找准螺纹,再顺时针稳稳拧进去,听到木材发出细微的“吱呀”声,就知道到位了。每个榫卯对接的瞬间,那种严丝合缝的感觉,像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仪式。
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,除了午饭的十五分钟,我一直蹲在阳台。膝盖麻了就换个姿势,腰酸了就站起来活动几下。过程中想起很多事——小时候看父亲做木工,他总说“慢工出细活”;第一次自己修自行车,满手油污却特别开心。这些记忆像从很远的地方飘回来,落在每一个正在拧紧的螺丝上。
当最后一块背板装好,我扶着椅子边缘,轻轻往前一推——它真的摇了起来。前后,前后,弧度平滑,没有半点卡顿。那个瞬间,所有疲惫都消失了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,看夕阳的光穿过新装的椅背,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影子。
妻子下班回来,我让她闭上眼睛。牵着她走到阳台,说“可以看了”。她愣了几秒,然后慢慢坐上去。摇椅轻轻晃动,她笑起来:“真结实啊。”
是啊,真结实。之后这些年,它承载过很多重量——妻子怀孕时在上面读育儿书,孩子出生后她抱着宝宝轻轻摇,父亲来看我们时喜欢在上面打盹,甚至家里那只胖猫也经常霸占着晒太阳。每年夏天我都要检查一遍螺丝,紧紧该紧的地方,五年过去了,它还是那么稳当。
现在写这些时,我正坐在这把摇椅上。稍微一动,它就发出熟悉的“嘎吱”声,不刺耳,像老朋友的招呼。阳台外的香樟树长高了不少,阳光的角度也变了,但摇椅还是老样子。
我常想,生活中有些东西就是这样——你亲手组装的不只是一件家具,还是一段时光。那些拧过的螺丝、对准的榫卯、调试的弧度,都成了记忆的坐标。每当坐在上面轻轻摇晃,仿佛能听见那个周末的声音:螺丝刀与螺丝的摩擦声,木板落地的轻响,还有自己专注的呼吸。
这摇椅之所以结实,大概不只是因为装得好。更是因为从第一个零件开始,它就承载了承诺、耐心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——想让在乎的人有个舒适的角落,想证明自己可以完成某件事,想在这个速食时代里,亲手创造一点能够长久陪伴的东西。
它还在轻轻摇着,像永远不会停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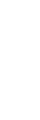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