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杨是我大学同学。报到第一天,我上铺,他下铺。我有点近视,正眯着眼睛整理床铺呢,他递过来一瓶水,“喝口水再弄吧。”就这么认识了。后来四年,我们一块儿在图书馆熬夜复习,一块儿在操场喝酒到天亮,他失恋了我陪他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,我找工作碰壁他二话不说把生活费分我一半。毕业了,我们留在同一座城市,虽然各自忙,但隔三差五总要聚一聚。我知道他胃不好,他知道我讨厌洋葱。这种交情,我以为是一辈子的。
那是个周五下午,他打电话来,声音有点急,说要去见个挺重要的客户,谈个项目,成败在此一举。但他那副戴了好几年的旧眼镜,前天不小心一屁股坐断了,临时去眼镜店配,度数不准,戴着头晕。“你那副备用的,黑框的那副,先借我应应急,撑个场面。谈完就还你,最晚明天。”他说得又快又急,背景音是嘈杂的街道。
我能说什么?当然说行。那副备用眼镜我挺喜欢的,镜腿儿上还有道细小的划痕,是我有次爬山不小心蹭的。但我没犹豫,立刻把放眼镜的盒子找出来,约了地方给他送过去。见到他时,他穿着西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但眼神里透着疲惫和焦虑。我把眼镜盒递给他,他接过去,拍了拍我肩膀,“谢了兄弟,这回要是成了,请你吃大餐。”他打开盒子,戴上眼镜,还扶了扶镜框,对我笑了笑。那笑容,和大学时一样,带着点依赖和信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匆匆消失在街角,心里还替他鼓劲儿,希望他项目能谈成。
谁想到,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第二天,他没联系我。我想着可能项目谈得久,或者累了在休息,没在意。过了周末,还是没动静。我发微信问他项目怎么样,没回。打电话,响了很久,无人接听。一开始,我压根没往“不还”上想,净往坏处想了: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病了?遇到麻烦了?我甚至有点生气,这老杨,真不够意思,有事也不说一声,让人干着急。
我联系了我们另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刘。大刘也挺纳闷,说老杨最近好像是在折腾什么项目,神神秘秘的,但也有一阵子没联系了。我们又找了几个同学,都没消息。那种感觉很奇怪,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,一个和你分享了十年青春岁月的人,就像一滴水蒸发了一样,无影无踪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的担忧渐渐变成了困惑,然后是隐隐的受伤。我开始意识到,他可能不是出了事,他可能就是……不想联系了。可为什么?就因为一副眼镜?这说不通啊。那副眼镜是值点钱,但对我们这份交情来说,根本不算什么。他要是真困难,开口跟我说,眼镜送他都行,我眼皮都不会眨一下。
我时不时会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,最后一条就是我问他项目怎么样的那条,孤零零地悬在那里,没有回应。我反复回想那天见他的每一个细节,他的表情,他说的话。除了着急,似乎也没什么异常。难道那天的“借眼镜”,本身就是一个借口?一个为了切断联系而找的,最生硬、最蹩脚的借口?我不敢深想。
没有那副备用眼镜,确实有点不方便。有次出差,常用的眼镜掉酒店洗手池里,镜片裂了,那一刻我特别抓狂,下意识就想,要是那副备用的在就好了。这个念头冒出来,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
大刘后来打听到一点模糊的消息,说老杨好像去了南方一座城市,具体做什么不清楚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活着,他好好的,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方式,从我的生活里退出。我们之间,没有争吵,没有矛盾,甚至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。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实物联系,就是那副在他手里的,我的黑框眼镜。
我现在偶尔还会想,那副眼镜,他后来还戴着吗?他戴着的时候,会不会偶尔想起我?想起我们挤在宿舍里分一碗泡面的日子,想起我们吹过的牛,发过的誓?也许,那副带着我度数、镜腿上有划痕的眼镜,对他而言,就像我们这段友谊一样,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,用完了,也就失去了价值,连带着过去的一切,都可以轻易丢弃。
我终于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:有些人,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只是,我没想到我和老杨的这段路,会以这样一种无声的方式戛然而止。丢了一副眼镜,看清一个人,断了一段十年情谊。说起来轻巧,可这代价,对我来说,真的太沉重了。那副眼镜,就像一个沉默的证人,它见证过我们最真挚的岁月,也见证了一场最潦草的离散。它现在在哪儿,是什么命运,我不知道,也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我心里那个叫“老杨”的位置,从此空了一块,凉飕飕的,再也暖和不起来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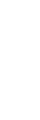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