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的我,是个连青菜都会煮烂的厨房杀手。我的拿手菜是泡面,能变出的花样无非是加个蛋,或者丢几片青菜叶子。出租屋的厨房角落里,永远堆着各种口味的泡面箱。
妈妈的教学是从最基础的开始的。“先学会站,”她拍拍我的后背,“别弓着腰,站直了,手腕才使得上劲。”她教我怎么握刀——食指按在刀背上,其他手指弯曲抵住食材。“手腕动,胳膊不动,”她握着我的手切土豆丝,“这样切出来才匀称。”
那个土豆,我切了整整四十分钟。先是厚薄不一的片,再是粗细不匀的丝,案板上堆满了歪歪扭扭的土豆条。妈妈就在旁边看着,偶尔伸手调整我握刀的姿势。“不急,”她说,“刀要稳,心要静。”
第一道真正完成的菜,是那道西红柿炒鸡蛋。
打蛋时我太用力,蛋壳掉进了碗里;切西红柿时汁水溅得到处都是;油烧得太热,蛋液下锅“刺啦”一声,吓得我往后跳了一步。妈妈不慌不忙地接过锅铲,动作流畅得像在跳舞。她教我听油的声音——太响就是火大了,没声音就是火小了。她教我看蛋液的状态——刚凝固就要划散,这样才嫩。
当我终于把那盘红黄相间的菜端上桌时,手指上还贴了两个创可贴——切西红柿时划的。但看着家人吃下去时满足的表情,那种成就感,是泡面永远给不了的。
接下来的每个周末,我都雷打不动地回家学做菜。从清炒时蔬到红烧肉,从煲汤到包饺子。妈妈的教学很有章法——先学炒,再学烧,然后学蒸、炖、煮。
学做红烧肉时,我在糖色前败下阵来。看着冰糖在锅里融化,从透明到浅黄,再到焦糖色,我总掌握不好时机。不是炒得太浅颜色不够,就是炒过头了发苦。妈妈站在旁边,在我手忙脚乱时说:“现在,就是现在,下肉!”那一瞬间,锅里腾起的香气,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“火候”。
最难忘的是学包饺子。我和的面不是太硬就是太软,擀的皮厚薄不均。妈妈手把手地教我怎么转着擀面杖,怎么让皮中间厚四周薄。包馅的时候,我总捏不紧边,一下锅就煮成了一锅片汤。妈妈笑了:“你呀,就是太着急了。捏饺子要用心,一下是一下。”
那个冬天,我们包了无数个饺子。当终于有一批饺子能完整地出锅时,爸爸吃了一大盘,说这是他吃过最香的饺子。我知道他在鼓励我,但看着那些虽然歪歪扭扭却终于成型的饺子在盘子里冒着热气,我的眼眶还是湿了。
半年后的春节,我主动提出要准备年夜饭。
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:泡发香菇、海参,焯烫蹄筋,腌制排骨。年夜饭那天,我在厨房里从早忙到晚。
妈妈偶尔进来看看,但大多时候只是站在门口微笑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地指导,只是在我犹豫时提点一句:“鱼蒸八分钟就好。”“汤汁收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”
当最后一道菜上桌时,我看着满桌的菜肴——金黄的红烧鱼、油亮的红烧肉、翠绿的清炒时蔬、浓稠的佛跳墙—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自我的手。
爸爸举杯时说:“咱们家的大厨出师了。”妈妈却摇摇头:“不是出师,是入门了。做菜这门学问,一辈子都学不完。”
她转头看我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:“记住这个味道。以后无论你在哪里,只要会做这些菜,就永远有个家在身边。”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妈妈教给我的,远不止是做菜的技巧。她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,把家的味道、把生活的底气,一点一点地传给了我。那些下午,我们一边切菜一边聊天的时光;那些失败后又重来的坚持;那些油盐酱醋间的分寸拿捏——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对生活最真切的理解。
现在,我也系上了围裙,在自家的厨房里忙碌。当切菜的节奏变得从容,当调味的配比了然于心,我总会想起妈妈系着碎花围裙的样子。
泡面早已从我的生活中淡出。不是因为它们不好吃,而是因为我尝过了亲手创造的味道——那种从食材到菜肴的蜕变,那种让所爱之人展露笑颜的满足,是任何速食都无法替代的。
厨房还是那个厨房,但因为我学会了做菜,这里不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地方,而成了我能量的源泉、创意的工坊、情感的寄托。每当遇到烦心事,我就系上围裙,在切切炒炒中,心会慢慢静下来,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。
妈妈说得对,做菜是一辈子的事。而我很庆幸,在那個普通的周末下午,我走进了厨房,从打第一个鸡蛋开始,开启了这个温暖我一生的旅程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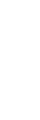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