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很普通的手机充电器,白色的方块头,上面那个小小的闪电标志都快被磨平了。线也不是原装的了,是后来在某宝上买的,他说原装线太贵,这根一样好用。线的胶皮在靠近插头的那一小段,已经有些开裂,露出里面细细的铜丝,他用绝缘胶带仔仔细细地缠了好几圈,缠得有点丑,但很结实。我记得他当时一边缠一边还跟我炫耀,说:“看咱这手艺,又能坚持大半年。”
这充电器,插在那里,好像他人还没走,只是去上个厕所,或者去客厅倒杯水,下一秒就会趿拉着拖鞋,啪嗒啪嗒地走回来,伸手拔下它,给那个永远电量告急的手机续上命。他的手机,电量好像永远撑不过半天。微信消息叮叮咚咚地响个不停,不是客户就是同事,要么就是那帮约着打球、喝酒的哥们儿。晚上躺床上,他总要刷上好一会儿视频,游戏解说、篮球集锦,或者是些我完全看不懂的军事新闻,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,明明灭灭的。我总嫌那光晃眼,影响我睡觉,会嘟囔一句:“快睡吧,别玩了。”他总是“嗯嗯”两声,手指却还在屏幕上划拉着。
有时候,他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,家里反而会获得片刻的宁静。他会有点焦躁,像丢了魂似的,在屋里转悠两圈,然后问我:“我充电器呢?就床头那个,看见没?”我就会没好气地回他:“不就在老地方插着嘛!离了它你是不是活不了?”现在想想,我那带着埋怨的语气里,其实也藏着一点点被他需要的小小满足感。
这个插座,这个床头柜,曾是我们这个小世界里最烟火气、最真实的角落。柜子上除了他的充电器,还放着他的眼镜盒,一个磨掉了漆的Zippo打火机(他虽然为我戒了烟,但这个打火机却一直留着),还有我们俩的结婚照。充电器的线,常常会缠住眼镜腿,或者压在那本他永远只看前几页的书上。每天清晨,我都是在手机充电完成的“嘀”声,或者是他摸索着拔插头的声音里醒过来的。那声音,和窗外的鸟叫、楼下早餐车的轱辘声一样,构成了我生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。
他走得太突然了。急性心肌梗死,医生是这么说的。头天晚上还好好的,我们一起看了个综艺,他还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临睡前,他像往常一样,把手机插在了那个充电器上。屏幕亮起,显示开始充电,那个小小的电池图标被绿色慢慢填充。他转过身,很快就睡着了,呼吸平稳。谁能想到,那竟是他最后一次给手机充电,也是我最后一次,听着他熟悉的鼾声入眠。
第二天早上,叫醒我的不是充电完成的提示音,也不是他起床的动静,而是可怕的、死一般的寂静。然后,就是一片混乱,120刺耳的鸣笛,医护人员匆忙的脚步,我语无伦次的哭喊……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。
等所有喧嚣都归于沉寂,等我从浑浑噩噩中稍微回过一点神,我才重新注意到这个房间,这个床头柜。其他东西好像都蒙上了一层灰,失去了光彩,唯有那个充电器,它还那么插着,仿佛时间的指针在那一刻之后,就再也没有走动过。线还是那样垂着,胶带缠着的地方还是那个角度,好像它的主人只是出门远行,总有一天会回来,顺手把它拔下来,揣进口袋里。
我没有动它。我没办法动它。收拾他衣物的时候,我把他的衬衫、裤子、外套一件件叠好,放进箱子,准备捐掉。那些东西上虽然也有他的气息,但它们是“死”的,是静止的。唯独这个充电器,它不一样。它曾经是能量的源泉,连接着他与外面那个热闹的世界,也维系着我们之间最日常、最琐碎的牵绊。它插在那里,就代表着一种“待机”状态,好像我们这个家,也只是暂时进入了“休眠”,随时可以被唤醒。
有好几次,我半夜醒来,迷迷糊糊中,看到那个插着的充电头,心里会猛地一悸,以为他回来了。清醒之后,那种失望像冰冷的潮水,一遍遍冲刷着心脏。我也试过给自己做心理建设,告诉自己,人走了,东西也该清理了,生活总要继续。我甚至有一次,手指已经碰到了那个充电头,冰凉的触感。可我使不上劲,就那么一点点把它拔出来的力气,我都没有。那感觉,不像是在拔一个电器,像是在亲手掐断最后一点念想,最后一丝微弱的、连接着过去的电流。
朋友来家里看我,总会委婉地提醒:“那个充电器,一直插着也不安全,还费电。”我点点头,说“知道了”,回头依然让它插在那里。他们不懂,那点电费,那微不足道的安全隐患,与我从中汲取的那点虚幻的温暖相比,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它就像一座无声的纪念碑,立在我的床头,纪念着那些我曾经嫌吵、嫌烦,如今却求之不得的日常。
昨天下午,阳光很好,我从外面回来,推开卧室门。一缕斜阳正好照在床头,那个白色的充电器头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光晕,垂下的电线在光里投下细细的影子。那一刻,我心里忽然不是那么痛了。我走过去,没有试图去拔它,而是伸出手,轻轻握住了那个他缠着胶带的地方。胶带表面已经没有了温度,但那种粗糙的触感,却异常真实。
我就那么站着,握着那段胶带,好像握着他曾经留在这里的体温和耐心。这个充电器,大概会一直插在那里吧。直到哪一天,它的线彻底老化断裂,或者这个插座坏掉。又或者,直到哪一天,我终于拥有了足够的勇气,能够平静地把它拔下来,收进那个属于他的盒子里,并且真心地相信,他不再需要它了。
但,不是今天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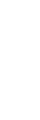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