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就那么斜斜地,带着点慵懒的劲儿,靠在我家沙发最左边的角落。米白色的亚麻布面,因为被靠得太多次,已经起了些细密的毛球;右下角还有个不太显眼的咖啡渍,是去年冬天他看球赛太激动时不小心泼上去的。当时他还手忙脚乱地拿纸巾擦,嘴里念叨着“完了完了”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说没事的,洗洗就好了,其实后来也没完全洗掉——现在想想,幸好没洗掉。
这个位置,是他专属的。
三年前搬进这个家时,我们一起去宜家挑的沙发。他试坐了好几个,最后选定这款深灰色的布艺沙发,理由特别实在:“腰靠在这儿刚好,脖子也能枕着。”然后他把自己那个有点旧的抱枕——就是我们大学时一起在夜市上买的,二十块钱一个——郑重其事地放在了最左边。他说这个位置离窗户近,下午有阳光照进来,暖和;离插座也近,方便给手机充电。
于是这三年,每个晚上,他都会窝在那个角落。
我做饭的时候,他就靠在那儿看书,偶尔抬头跟我说今天单位里的趣事;吃完饭,我们并排坐着看电影,他的脚总会不自觉地搭在茶几边上,轻轻晃着;周末的午后,他常在那里打盹,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呼吸均匀,怀里的抱枕随着他的胸口一起一伏。有时候我半夜醒来,会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回沙发上睡着了,笔记本电脑还亮着,抱枕被他搂在怀里——他说在沙发上灵感来得快,很多方案都是在深夜的沙发上完成的。
那个角落,因为他的存在,沙发垫子比其他地方塌陷得更深一些。亚麻布面被他常年靠着的地方,颜色也似乎更深一点,带着人体的温度和油脂慢慢浸润的痕迹。我试过坐在那里,却总觉得不对劲——靠背的角度,扶手的高度,甚至阳光照射的角度,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。我在那里坐不到十分钟就会腰酸,只好悻悻地挪回中间的位置。
他离开的那个早晨,把这个家收拾得异常整洁。碗洗了,地拖了,垃圾倒了,连阳台上的花都浇了水。只有这个抱枕,还保持着原样——微微凹陷,有点歪斜,仿佛他只是起身去倒杯水,随时都会回来,重新把自己埋进这个柔软的角落。
刚开始那几天,我动过把它收起来的念头。眼不见心不烦嘛,大家都这么说。可我的手每次碰到它,就会想起他靠在上面的样子——眯着眼睛笑的样子,皱着眉头思考的样子,累极了闭目养神的样子。最后我还是没动它,就让它留在那里。早晨起床,我会下意识地朝那个方向看一眼;晚上回家开门,第一眼也是先看那个角落。看见抱枕还在老地方,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安定一下。
朋友们来家里,总会小心翼翼地问:“要不要把那个抱枕收起来?”我摇摇头。他们大概觉得我在睹物思人,在自我折磨。其实不是的。这个抱枕在那里,这个属于他的角落还在,这个家就还是完整的模样。它像一个小小的坐标,锚定了这个空间里关于他的所有记忆。如果连这个最后的坐标都移走了,我怕这个家会真的变成一所空房子,而不仅仅是他暂时离开的地方。
上个月大扫除,我把它拿起来拍了拍灰。抱枕套该洗了,可我犹豫了很久,最后还是只用了湿毛巾轻轻擦拭。我怕洗得太干净,会把他留下的最后一点气息也洗掉——那种淡淡的,混合了洗发水和一点点汗味的,独属于他的味道。现在虽然已经很淡很淡了,但把脸埋进去仔细闻,好像还能捕捉到一丝痕迹。
这个米白色的抱枕,就这样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静默的参照物。它告诉我,有些东西没有变,有些位置还在等待,有些习惯已经刻进了生活的肌理里,不是轻易就能抹去的。
昨天下午,阳光很好,像极了他常在这里打盹的那些周末。我泡了杯茶,第一次尝试着在他那个位置坐下。确实不舒服,腰是悬空的,脖子也没地方靠。但我没有马上起来,就那样坐着,看着房间里熟悉的一切——从这个角度看去,电视机的反光刚好不会刺眼,能看见厨房里我忙碌的侧影,窗外的梧桐树也正好填满整个窗框。
原来,他选择了这个家里最好的一个角落。
茶凉了,我起身,把抱枕重新放好,轻轻拍了拍,让它恢复那个微微倾斜的角度。然后我回到沙发中间我的位置,继续看我的书。屋子里很安静,只有挂钟的滴答声。那个米白色的抱枕依然斜斜地靠在最左边,像一个温柔的句读,标注着这个故事尚未结束的篇章。
它就在那里,在老地方。而我知道,只要它还在那里,这个家就还在等待着,相信着,某一天门会打开,那个熟悉的身影会走进来,很自然地走向那个角落,把自己陷进沙发里,顺手捞过那个抱枕塞在腰后,然后抬头对我笑笑,说:
“我回来了。”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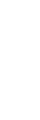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