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切,都因为他。
他是我父亲。一个对甜食挑剔到近乎固执的人。
他最爱的是老式奶油蛋糕——不是现在流行的动物奶油,就是最传统、最质朴的那种硬奶油,甜得直白,油润扎实。蛋糕胚要蓬松带点粗糙气孔,夹层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黄桃罐头和菠萝块,最上面要撒厚厚的椰丝,还有几颗染得鲜红的樱桃。
我第一次给他买生日蛋糕,挑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最终选了个看起来最时髦的——黑森林,用顶级的淡奶油,酒渍樱桃,苦甜巧克力屑。我以为这更高档,更健康。
他尝了一口,细细在嘴里抿着,然后点点头,说:“挺好。”可那整整八寸的蛋糕,直到最后干裂发硬,三分之二都进了垃圾桶。我妈后来悄悄告诉我:“你爸说,吃不懂,苦溜溜的,还是老式奶油香。”
那一刻我才明白,我那自以为是的“更好”,在他那里,全是错付。
我开始认真研究他口中的“好吃”到底是什么。那家他偶尔会提起的、在城南的老字号蛋糕店,成了我的目的地。店面很旧,玻璃柜台磨花了边,空气里弥漫着甜腻腻的香气,混合着奶香和鸡蛋香。
我买了最小尺寸的鲜奶蛋糕。老板娘动作麻利,舀起一大勺雪白的硬奶油,抹得厚厚的,几乎看不见下面的蛋糕胚。她问我:“小姑娘,要写个字不?寿,或者福?”
我摇摇头,心里有点酸。我只是想买给他吃,不需要任何由头。
那天晚上,我把蛋糕放在桌上。他正看着电视,瞥了一眼,没说话。但广告间隙,他拿起旁边的小叉子,切下一角,送进嘴里。我紧张地看着。
他咀嚼得很慢,眼睛微微眯了一下,那是他舒服时常有的表情。然后,他又切了一角,这次,叉子精准地叉起了一块浸过糖水的黄桃。
“嗯,”他终于开口,像是自言自语,“是这个味儿。”
就这一句话,我悬着的心,轰然落地。那是一种比任何夸奖都让我满足的肯定。从那以后,我成了那家老店的常客。我不再只在生日或节日才买,而是隔三差五,在他加班晚归时,在他看起来有些疲惫时,或者,仅仅是因为我想看他吃下第一口时,那微微眯起的眼睛。
我摸清了他所有的偏好:椰丝要多,樱桃两颗正好,黄桃比菠萝更得他心。老板娘都认识我了,每次我去,她不用我问就会说:“今天奶油打得特别好,给你爸带的?”
我点点头。那种感觉,就像我们共享着一个甜蜜的秘密。
我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很长,长到我可以把他宠成一个更挑嘴的老头。
可是,病来得毫无征兆。
检查,住院,手术。医院的白墙吸走了所有的色彩和味道。他迅速消瘦,食欲变得极差。有一天,他难得有精神,忽然对我说:“有点想吃……甜的。”
我几乎是冲出医院,开车直奔城南。那天堵车堵得厉害,我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,心急如焚。我怕去晚了店关门,更怕他那一刻想吃的念头,转瞬即逝。
当我终于捧着那一方小小的、雪白的蛋糕赶到病房时,他的手已经没什么力气。我扶着他,用小勺挖了顶上最软、带着椰丝的那一口,送到他嘴边。
他含住了,抿了很久,然后很轻、很轻地笑了一下。
“甜。”他说。
那是他最后一次尝到甜味。几天后,他永远地睡着了。
处理完所有后事,生活仿佛被抽空了。有一天,我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家老店。老板娘看到我,像往常一样笑着招呼:“来啦?今天奶油好,给你……”话没说完,她看清了我的神色,和我一身还未褪尽的黑衣,笑容僵在脸上,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我站在那里,看着柜台里一模一样的老式奶油蛋糕,它们依然那么饱满,那么诱人。可我知道,我再也无法买下其中的任何一个了。
因为那个唯一会为它眯起眼睛的人,不在了。
我买给谁吃呢?
“我再也没买过。”这句话,成了我心里一道无声的禁令。它不仅关乎一种蛋糕,更关乎我所有想要与他分享的冲动。看到新开的甜品店,读到推荐菜谱,遇到他可能会喜欢的点心……所有这些念头刚刚冒头,就会被这句无声的话轻轻压下去。
那个唯一的、最忠实的品鉴者缺席了,我的这份心意,便彻底失去了投递的地址。
家里的口味也渐渐变了。母亲开始注重养生,嫌以前的蛋糕太甜太油。孩子们更是从小吃着低糖的慕斯和芝士蛋糕长大,他们对爷爷挚爱的那口奶油,评价是:“腻。”
它成了只属于我和父亲的,一个被时代渐渐遗忘的味觉契约。
去年他生日,我独自去了墓园。深秋的风已经很凉,吹得四周的松树呜呜作响。我空着手去的,什么也没带。我知道,带什么都是多余的形式。
我就站在那里,跟他说了很久的话。说家里的琐事,说孩子的成长,说我的烦恼和一点点成绩。最后,我对着那块冰冷的石碑,轻轻地说:
“爸,城南那家店,还在开着呢。奶油,还是那么白,那么厚,椰丝撒得满满的。”
风穿过松枝,声音像极了一声悠长的应答。
那一刻我忽然懂了,“我再也没买过”,并不是一种决绝的告别,而是最深沉的纪念。我把那个味道,完好无损地封存在了记忆里,它没有被后来任何一次寻常的品尝冲淡、混淆或改变。它还是他最后一口尝到的,那个纯粹的、极致的甜。
那个味道,连同他眯起眼睛的样子,一起被我做成了琥珀,晶莹剔透,永不变质。
所以,就让它留在那里吧。留在城南那间旧店铺的玻璃柜里,留在过去那些温暖的夜晚里,留在他微微扬起的嘴角上。
我不再去买,是因为那个蛋糕,早已在我心里订了终身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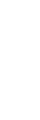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