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,我和熬夜的缘分,是从大学开始的。那时他在隔壁宿舍,总在深夜发来消息:“睡了吗?”而我总是秒回:“还没。”然后我们就能聊到凌晨两三点,从专业课聊到人生理想,从食堂的包子聊到遥远的星空。毕业后合租,熬夜成了我们的日常。他是设计师,我是写手,两个夜猫子相得益彰。
我们的出租屋不大,但有个朝南的阳台。深夜时分,我们会泡一壶茶,搬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。他看着设计稿,我敲着键盘,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。楼下街道渐渐安静,只有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说深夜的灵感最鲜活,我说夜晚的思绪最清晰。其实现在想来,或许我们只是贪恋这份只属于彼此的宁静。
记得有个雨夜,他赶一个紧急方案,我陪着他熬夜。凌晨三点,他突然放下数位板,说想吃火锅。我们真的就撑着伞,在雨中走了二十分钟,找到一家二十四小时火锅店。热腾腾的雾气里,他的眼镜片蒙上一层白雾,我们像两个逃课的高中生,为这深夜的疯狂窃喜。回去时天已微亮,他说:“以后每个熬夜的夜晚,我们都要找点乐子。”
他真的做到了。有时是突然播放一首老歌,拉着我在客厅里跳舞;有时是变魔术般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还热乎的茶叶蛋;有时只是走到我身后,轻轻按摩我僵硬的肩膀。这些小小的惊喜,让熬夜变成了一种期待。
可这一切,在他离开后都变了。
他走得很突然——公司外派他去国外总部,为期三年。临走前那个晚上,我们照例熬夜,但谁也没说话。他整理行李,我假装写稿,其实文档上一个字都没打出来。凌晨四点,他合上最后一个行李箱,走到我身边说:“别老是熬夜,我不在,没人给你泡枸杞茶了。”
我笑着点头,心里却想:没有你的夜晚,我怎么可能熬夜?
果然,他走后的第一个晚上,我八点就洗漱上床了。躺在床上,听见隔壁传来电视剧的声音,楼下有情侣在道别,远处还有汽车驶过——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,因为往常这个时间,我正对着发光的屏幕,他在旁边画图,我们的世界只有彼此。
起初,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。毕竟熬夜这么多年,身体都有生物钟了。可一天天过去,我竟然真的不再熬夜。晚上十点,眼皮就开始打架;十一点,已经进入梦乡。朋友听说后都很惊讶:“你这个资深夜猫子,居然从良了?”
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试着在深夜打开过文档,可敲出的每个字都显得那么生硬。泡了他常买的那个牌子的茶,喝起来却索然无味。阳台上的椅子收起来了一把,因为一个人坐在那里,夜风显得特别凉。
有一次,我强迫自己熬夜赶稿。到了十二点,习惯性地转头想说什么,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椅子。那一刻,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,酸楚从心脏蔓延到指尖。我匆匆保存文档,关灯上床。黑暗中才明白——我不是不能熬夜,我是不敢。每一个深夜都会让回忆变得格外清晰,每一个习惯性回首都让失去更加具体。
慢慢地,我发现了早睡的好处。早晨的空气特别清新,早餐店的包子刚出笼,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会对我微笑。我开始在清晨写作,发现思路反而更清晰。阳光透过窗帘洒在键盘上,鸟鸣代替了曾经的深夜寂静。
只是偶尔,在整理东西时,会翻出我们熬夜的“罪证”——一叠外卖单,都是凌晨两点后的订单;他画满草图的速写本;还有那个我们一起在夜市淘来的马克杯,杯壁上印着“夜猫子联盟”。
如今,他离开已经一年了。我们依然每天视频,只是都在彼此的白天。他的下午,我的晚上。屏幕那头的他看起来有些疲惫,但总会问:“今天早睡了吗?”我点点头,然后我们都笑了。
原来,熬夜从来不是目的,而是我们在茫茫人海中,为彼此点亮的那盏灯。当那个值得陪伴的人不在身边,深夜就只是深夜而已。
前几天整理书柜,发现他留给我的一本素描本。翻开来看,每一页都是熬夜时的我——趴在桌上小憩的侧脸,对着屏幕皱眉的样子,喝茶时被烫到的滑稽表情……最后一页画的是一盏台灯,灯光在纸上晕开温暖的光晕,下面有一行小字:“愿所有的深夜,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。”
合上素描本,窗外阳光正好。我给自己泡了杯茶,打开文档开始工作。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早睡早起,再也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熬夜到天明。
但我知道,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,如果有一天他再在深夜发来那句“睡了吗”,我依然会秒回——
“还没。”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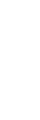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