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,家里的月饼总是不够分。那时物质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,一盒月饼四个,豆沙、五仁、枣泥,最金贵的就是那个双黄白莲蓉。每到分月饼时,我们兄妹三个就眼巴巴地围着桌子。
“我要莲蓉的!”小弟总是第一个喊出来。
“我也要!”妹妹紧跟着。
我作为老大,只能抿着嘴不说话,眼睛却死死盯着那个油亮亮的月饼包装。
母亲会把月饼切成六份——父母各一份,我们三个孩子各一份,还有一份再切成三小块。分月饼是门学问,母亲拿着刀,小心翼翼地比划着,务求每块都带着等量的蛋黄和莲蓉。
“你是哥哥,让着弟弟妹妹。”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。
于是,莲蓉最多的那块永远轮不到我。
只有爷爷会悄悄把我叫到一旁,从他那份里掰一大块莲蓉塞进我手里。
“快吃,别让他们看见。”他眨眨眼,皱纹里都是笑意。
那口莲蓉特别甜,细腻柔滑,在嘴里慢慢化开,带着蛋黄的咸香。我小口小口地抿着,想让这份甜停留得久一些。
后来我才明白,爷爷也最爱吃莲蓉。他把最多的那份给了我,自己只啃着边缘的面皮。
日子一年年过去,我们陆续长大、离家。中秋渐渐变成了电话里的问候,和快递到各处的月饼礼盒。我留在老家工作,陪在爷爷身边。
他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先是上下楼需要扶着栏杆歇两次,后来发展到出门买菜都要带着折叠凳,走一段就得坐下来喘口气。记忆最深刻的是去年中秋前,我陪他去体检,医生看着片子直摇头:“老人家这肺啊,就像用了太久的毛巾,到处都是破洞了。”
那个中秋,我买了好几盒最高档的双黄白莲蓉。拆开包装时,爷爷的眼睛亮了一下,随即又黯淡下去。
“医生说了,要控制糖分。”他摆摆手,“你们吃吧。”
可我知道,他是舍不得。一辈子节俭惯了,看见好东西第一反应总是留给儿孙。
我执意拆开一个,切成小块。
“爷爷,今天就破例一次。”我把带着完整蛋黄的那块递给他。
他犹豫了一下,接过去,像孩子般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,在嘴里含了很久。
“还是那个味道。”他眯起眼睛笑了,“你记得吗?你小时候……”
那个下午,我们爷孙俩就着茶水,慢慢吃完了一整个月饼。他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,有些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,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色。
今年开春后,爷爷的身体急转直下。住院的那些日子,他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。有次我削了苹果,切成极小的丁喂他,他也只是象征性地含一下就吐了出来。
直到中秋前半个月,他忽然有了些精神,拉着我的手说:“今年……还想吃口莲蓉月饼。”
我飞奔到楼下最好的糕点店,买了刚出炉的莲蓉月饼。回到病房时,他却已经睡过去了,呼吸轻得几乎看不见。
护士说:“刚才醒了一会儿,又累了。”
我把月饼放在床头柜上,想着等他醒来就能吃到。
可他再也没能醒来。
中秋那天,我独自坐在曾经一起分月饼的老屋里。桌上放着那盒精致的双黄白莲蓉——是爷爷走后收到的礼物。我拆开包装,金黄的月饼在月光下泛着油光。
我习惯性地把月饼掰开,露出饱满的莲蓉和油亮的蛋黄。手伸向另一半时,才突然意识到:再也没有人跟我抢莲蓉馅了。
我试着咬了一口。莲蓉还是那么细腻香甜,在舌尖慢慢融化。可不知为什么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是少了那个会把自己那份留给我的老人;少了那份被谦让的温暖;少了切月饼时那份小心翼翼的珍重。
原来,食物的味道从来不只是味道本身。它包裹着时光,浸润着记忆,和那些与我们分享的人紧紧相连。当那些人离开后,再美味的食物,也只剩下了一半的滋味。
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,和去年一样温柔。我把剩下的月饼仔细包好,放进冰箱——这是爷爷教我的习惯,好东西要慢慢吃。
只是这一次,再也没有人会悄悄来到我身边,把最多的莲蓉馅留给我了。
而我,终于成了那个会把莲蓉馅让给别人的人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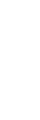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