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刚入行那会儿,我以为拍照就是调好光圈快门,让孩子摆个姿势笑一个。第一次单独拍摄是个三岁的小男孩,妈妈提前说了“我儿子可乖了”。结果呢?一到影棚,孩子就像上了发条,满场跑。我跪在地上追着他拍,汗把衬衫都湿透了。最后妈妈不好意思地说:“要不改天吧?”那一刻我特别沮丧。
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可能是从学会蹲下来说话开始的。
现在每个孩子进来,我第一件事就是蹲下来,和他们一样高。“你的鞋子会发光耶!”、“哇,这件裙子是艾莎公主的吗?”——先成为他们眼中的“大朋友”,而不是那个举着黑乎乎相机的陌生人。
上周来了个小姑娘叫妞妞,四岁,扎两个羊角辫,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角。我拿出准备好的泡泡机,轻轻一吹——她的眼睛立刻亮了,像星星掉进了玻璃珠。我没有马上拍照,而是陪她玩了五分钟泡泡。当她终于伸手去抓泡泡,发出咯咯笑声时,我才悄悄举起相机。那张照片里,她的侧脸映着彩虹色的泡泡,睫毛上还挂着一点点好奇。妈妈看到成片时说:“这是我见过她最开心的样子。”
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宇宙。有的孩子是“慢热型”,你得等;有的是“探险家”,你得跟;还有的是“小思想家”,你得猜。
最让我难忘的是去年冬天的齐齐。五岁的男孩,自闭症谱系,几乎不说话。他妈妈提前发来很长的信息,说孩子对声音敏感,可能会捂耳朵。我回她:“没关系,我们慢慢来。”
拍摄那天,影棚特别安静,我把所有会发出声响的设备都包了软布。齐齐进来后一直蹲在角落,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。我观察了很久,发现他偶尔会用手在空气中画圈。
“齐齐是不是喜欢圆形的东西?”我轻声问他妈妈。
她愣了一下:“对啊,他特别喜欢转圈的东西。”
我立刻有了主意。找来一个水晶球音乐盒,轻轻转动。球里的雪花缓缓飘落,齐齐的视线第一次有了焦点。他慢慢走过来,但没有看我,只是盯着旋转的水晶球。
我没有急着拍照,而是坐在地板上,和他一起看那个水晶球。十分钟,二十分钟……当他终于伸出手指,轻轻触碰水晶球底座时,我按下了快门。
那张照片后来被妈妈设成了手机屏保。她说这是齐齐第一次主动探索世界的证据。对我来说,这张照片教会我:有些最美的瞬间,就藏在那些看似“异常”的行为里。
当然,不是每次拍摄都这么顺利。哭闹、尿裤子、突然要上厕所——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我的摄影包里,除了相机镜头,更多的是小饼干、贴纸和泡泡水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个“带着相机的幼儿园老师”。
上个月拍一对兄妹,妹妹两岁,哥哥五岁。拍到一半妹妹突然大哭,怎么哄都不行。我灵机一动:“我们来玩‘谁先逗笑妹妹’的游戏好不好?”哥哥立刻来了精神,做鬼脸、学动物叫,当妹妹终于破涕为笑时,我抓拍到了哥哥那个骄傲又宠溺的表情。那张照片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合影都来得珍贵。
这份工作做久了,你会慢慢懂得:孩子脸上的表情,就像四月天的云,一刻一个样。刚才还晴空万里,转眼就可能大雨倾盆。而我的任务,就是在那片云最美的时候,轻轻地把它留下来。
我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叫“魔法时刻”,存着那些无法复制的瞬间——第一次看到雪花的张大嘴巴,生日蛋糕上蜡烛吹灭时的满足,还有在妈妈怀里安心睡去的模样。这些照片没有完美的构图和光线,却是最真实的童年。
前几天翻看十年前拍的第一组照片,那个满场跑的小男孩,现在应该上初中了吧?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个追着他跑的摄影师叔叔。而我却通过镜头,见证了成千上万个孩子的成长片段。
有人问我,拍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技术?我说,不是多贵的相机,也不是多精妙的布光,而是你真的喜欢孩子,愿意花时间去等一朵花开。
明天又要拍摄了,是个刚满百天的小宝宝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柔软的毯子、适宜的温度,还有满满的耐心。谁知道这个小家伙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?每次举起相机,我都像第一次那样充满期待——因为每个孩子,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星星,而我何其有幸,能把这些星星的光芒,轻轻装进相框里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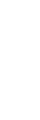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