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年春天,我们都忘了这回事。两个刚组建家庭的人,忙着应付房贷、工作,为谁洗碗谁拖地拌嘴。直到四月底某个周末,我拉开窗帘,突然看见院角那抹粉红——三株月季全开了,花朵不大,但挤挤挨挨的,在晨光里微微颤动。我光着脚跑出去,他在身后喊“小心扎着”,也跟着出来。我们蹲在花前看了很久,他伸手碰了碰花瓣说:“还真开了。”
从那以后,这些花成了我们生活的计时器。
第二年花开时,我怀孕了。孕吐最厉害的那段日子,是他每天去浇水。有天深夜我睡不着,看见他打着手电在院里,轻轻把被风吹歪的花枝扶正,又蹲下来和花说话:“你们要开好看点,她看了心情好。”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。
孩子出生在五月,正是月季开得最盛的时候。出院回家,他先抱孩子进屋,又折返出来,小心剪下开得最好的几朵放在我枕边。整个月子期间,窗台上的花瓶里总有新换的月季。他说:“你看,花和孩子一起来了。”
第三年,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次争吵。为孩子的教育问题,为两边父母,为所有琐碎得说不清缘由的事。有半个月,我们几乎不说话。那个春天雨水特别多,我注意到月季长了蚜虫,但赌气没说。后来发现他在悄悄喷药,还从网上学了用烟丝泡水治虫的土方子。花终于开了,虽然比往年稀疏。他剪下一朵放在我书桌上:“虫子治好了。”就那么一句话,所有的委屈都散了。
最难忘是第五年。他父亲病重,我们连夜赶回老家。在医院守了整整两周,再回家时已是初夏。推开院门,我们都愣住了——月季开得疯了似的,密密麻麻的花朵把枝条都压弯了,地上落满花瓣,像铺了层粉色的雪。邻居说:“今年这花开得特别好,一天比一天多。”我们站在花丛里,他轻轻说了句:“爸是不是看见了?”我握紧他的手,眼泪掉在花瓣上。
这些年,我们在花下给孩子过生日,在花香里和好,在花开时等出差的他回家。有一年他外派大半年,视频时总说:“让我看看花。”其实我知道,他是想通过花看看家。等他回来时已是秋天,月季居然又开了一轮,虽然只有零星几朵。他说:“这花在等我呢。”
现在,这些月季已经长成一大片,每年春天准时发芽,四月底准时开花。孩子从蹒跚学步到会拿着小水壶帮忙浇水,我们的白发从几根到需要定期染黑,唯有这些花,年年如约而至。
昨天傍晚,我们坐在院里看花。今年的第一朵刚刚绽放,其余的还都是花苞。他忽然说:“记得刚种下时,卖花的人说这种月季能活几十年。”我点点头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就像很多年前那个他深夜看花的晚上,只是影子从一个变成了三个——孩子正在花丛边追蝴蝶。
这些花不会说话,但它们什么都知道。知道我们怎样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,知道我们流过多少眼泪又笑了多少次,知道我们的头发怎样一天天变白,我们的手怎样在岁月里越握越紧。每年春天,当第一朵月季绽放时,我都觉得听见了时光走过的声音——很轻,很柔,像花瓣打开时的颤动。
也许世界上并没有永不凋谢的花,但如果有,大概就是这样的吧——种在相爱的人身边,用年年盛开来见证,最普通的日子怎样变成诗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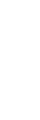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