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我只回了句:“知道了,别操心。”
现在想想,她总是这样,事无巨细地惦记着我的生活。而我,除了那句干巴巴的“别来无恙”,好像从来没能好好回应过她的关心。
她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,我们从穿开裆裤就认识了。小时候住大院,她家在我家斜对面。每年秋天,她妈妈做桂花糕,总会让她给我送一盘来。她端着盘子站在我家门口,小声说:“我妈让给的。”然后飞快跑开。其实我知道,是她自己非要多要一份,“给隔壁那个馋猫”,这是她妈妈后来告诉我的。
上初中那年,我爸工作调动,我们搬到了南方。临走前,她塞给我一个铁盒子,里面装满了桂花——那是她前一天晚上偷偷从树上摘下来晾干的。“你想家的时候就闻闻,”她说,“咱们大院秋天的味道都在里面了。”
那个铁盒子跟我走了很多地方,从初中到大学,从南方到更远的南方。桂花早就没了香气,可我还是留着。每次搬家收拾东西,看到它就会想起她站在桂花树下的样子,踮着脚,努力够着枝头。
大学四年,我们隔着两千公里。她总能在电话里听出我情绪不对。有一次我失恋了,半夜在阳台打电话,说着说着就哭了。她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,最后说:“你等着。”然后挂了电话。十分钟后,我的手机响了,她发来一段视频——是我们大院那棵桂花树,在月光下开着细细碎碎的花。“你看,桂花又开了,”她在视频里说,“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可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却总是后知后觉。大三那年,她父亲生病住院,她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。这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,她只是笑笑:“告诉你有什么用,你又回不来,白白担心。”
工作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。每次回老家,她都会来车站接我。见面的第一句永远是“别来无恙”,而她总是上下打量我一番,然后开始数落:“又瘦了”、“黑眼圈这么重”、“这件衬衫都旧了”。起初我觉得她啰嗦,直到有一次,我随口说喜欢吃她做的红烧肉,第二年回家,她竟然真的学会了,端上来的时候,手上还有烫伤的痕迹。
“练了多久?”我问。
“没几次,”她轻描淡写,“反正周末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后来她妈妈告诉我,她失败了好多次,不是糊了就是咸了,最后那锅成功的,是她凌晨五点爬起来做的。
去年冬天,我生了一场大病,住院两周。没告诉家里人,也没告诉她。出院那天,打开手机,几十条未读消息,最新的一条是:“你消失半个月了,我知道你肯定有事。接电话,不然我买机票飞过去了。”
我赶紧回电话,她接起来,什么都没问,只是说:“还好吗?”
“别来无恙。”我习惯性地回答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然后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:“你永远都是这句话。你知道吗,我宁愿听你说‘不好’,也不想听这句‘别来无恙’。”
那一刻,我握着手机,站在医院门口,突然明白了很多事。这些年来,她一直在用她的方式靠近我,关心我,而我却用一句“别来无恙”把她推开。不是不想回应,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就像小时候收到她送的桂花,明明心里欢喜,却只会说声“谢谢”,然后把铁盒子藏在抽屉最深处。
其实我有那么多话想告诉她:谢谢你记得我爱吃什么,谢谢你在我想家的时候让我听见大院里的风声,谢谢你看穿我的坚强知道我也会脆弱。可话到嘴边,只剩下那句苍白的“别来无恙”。
今天,她又要来接我了。火车缓缓进站时,我对着车窗整理了一下衣领。窗外,她已经等在那里,手里拿着一个保温盒——不用猜,肯定是她新学的什么拿手菜。
我走出车厢,她迎上来,还没开口,我就说:“这三个月过得不太好。项目压力大,经常失眠,特别想你做的红烧肉。”
她愣住了,眼睛慢慢亮起来,然后把保温盒塞进我手里:“还热着。这次加了点陈皮,你说过喜欢那个味道。”
保温盒热乎乎的,这股暖意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。原来,卸下那身故作轻松的姿态并不难;原来,接受一个人的关心,也是一种温柔。
站台上人来人往,我们站在那儿,谁也没急着走。她开始细数这三个月里发生的琐事:大院那棵桂花树生虫了,她想办法治好了;她养的那只猫胖了不少;她学会了做新的菜式……
我认真听着,偶尔插句话。这次,我没有说“别来无恙”。因为有些关心,值得用更真诚的方式回应;有些温暖,不该被轻描淡写地带过。
风吹过来,已经不那么冷了。春天就要来了,而有些改变,也许就从这一刻开始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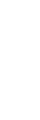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