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初只是细密的雨丝,穿过梧桐叶的缝隙,洒在脸上凉丝丝的。我靠在那棵老槐树粗糙的树干上,仰起头,看见灰蒙蒙的天空被枝叶切割成碎片。然后雨就大了,噼里啪啦地打在树叶上,打湿了我的衬衫。可我一步都不想挪。
这棵树真大啊,三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,枝叶茂密得像一把巨伞。我缩在树干后面,雨水顺着树皮的沟壑流下来,浸透了我的后背。可我觉得安全——这里没有人能看到我,没有人会问我怎么了,没有人会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可以尽情地哭,让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,分不清哪个更咸。
我哭得没有声音,只是肩膀在不停地抖。眼泪滚烫地流下来,在已经湿透的脸上划出新的痕迹。我死死咬着嘴唇,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。手里攥着手机,屏幕还亮着,显示着十分钟前收到的短信:“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对不起。”
就这么七个字。七年的感情,换来了七个字。
雨越下越大,从树叶间隙漏下的雨点变成了细流。我突然想起,我们第一次牵手,也是在这样一棵大树下。那是大学校园里的香樟树,夏天开满细小的花,风一吹,花瓣就簌簌地落下来。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,我也是。我们在树下站了很久,谁都不敢看谁,只是傻傻地笑着。
后来他总说,那棵香樟树是我们的见证。每年纪念日,我们都会回去,在树下的石头上刻一道痕。第一年刻了个爱心,第二年刻了我们的名字缩写,第三年……那些石头上的刻痕,现在想来,大概已经被风雨磨平了吧。
雨声哗啦啦的,整个世界都模糊了。我蹲下来,抱住膝盖,把脸埋进臂弯里。这样哭起来更痛快些,反正也没人看见。我想起去年冬天,他冒着大雪给我送退烧药,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,就因为我说不想一个人去医院。那时候他的睫毛上都结了霜,却还笑着摸摸我的头说“笨蛋,有我在呢”。
怎么就不在了呢?
上周我们还一起去吃了那家巷子深处的牛肉面,他细心地把香菜挑出来——我从来不吃香菜。他还记得我不吃香菜,却已经不记得要爱我了。人真是奇怪啊。
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,刺得生疼。我抹了把脸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远处有车灯扫过,黄色的光柱里,雨丝密得像一堵墙。偶尔有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,没有人注意到树后还有个哭成傻子的我。
也好。成年人嘛,总得有个地方可以暂时不用当成年人。
我哭得累了,就顺着树干滑坐下来,坐在湿漉漉的树根上。泥土的腥味混着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蚂蚁在我脚边忙碌地搬家,排成长长的一队,绕过我的运动鞋,继续它们的路程。它们的世界里,没有失恋这回事。
一只蜗牛慢吞吞地爬过一片落叶,背着它小小的房子。我突然很羡慕它——无论走到哪里,家都在身上。而我呢?那个我以为会是永远的家,就这么没了。
手机又震动了一下。我猛地抓起来看,是妈妈发来的:“闺女,这周末回家吗?妈给你包饺子。”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了,这次却不太一样。这个世界上,终究还是有人永远等着我回家的。
雨渐渐小了,从倾盆大雨变回了绵绵细雨。天边露出一丝微光,灰云开始散开。我哭得太久,眼睛肿得像核桃,头也一阵阵发疼。可奇怪的是,心里那块大石头,好像没有那么沉了。
我扶着树干慢慢站起来,腿麻得厉害,差点摔倒。老槐树的树皮粗糙而温暖,像一位沉默的长者的手掌。我轻轻拍了拍它,算是道别。
走出树荫时,阳光正好从云缝里漏下来,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。空气清新得不像话,每片叶子都被雨水洗得发亮。我深深吸了口气,满是雨后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
回到家时,妈妈正在厨房里忙活。看见我浑身湿透的样子,她愣了一下,什么也没问,只是拿来干毛巾:“快去洗个热水澡,别感冒了。”
我点点头,走进浴室。镜子里的人眼睛红肿,头发凌乱,狼狈得可笑。可不知为什么,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,轻轻笑了一下。
那棵老槐树,后来我又路过几次。每次都会多看它一眼,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。它还在那里,春去秋来,叶子绿了又黄。而我已经能够平静地想起那些往事,不再流泪。
有些伤口,时间真的能治好。而有些成长,非得经历一场大雨不可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南港文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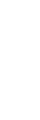 南港文典
南港文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37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27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6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4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2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